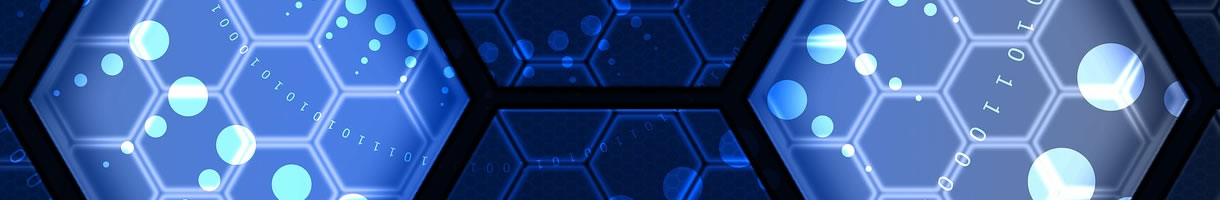土地革命战争故事:重返陕北

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发展红军和苏区,1936年2月,红一方面军以“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”的名义,从陕甘苏区东渡黄河进入山西,发起东征战役。
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调兵遣将,企图阻止红军东进。红军一面与晋绥军作战,一面大力开展群众工作,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,积极准备对日作战。
正当东征红军继续发展进攻时,蒋介石应阎锡山的请求,将国民党中央军10个师调入山西,配合晋绥军作战,企图将红军围歼于山西境内。
中共中央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,于5月5日发出《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》,指出:“国难当头,双方决战,不论胜负属谁,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,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。”同日,红军全部西渡黄河,返回陕甘苏区休整。
留在晋中的少数红军游击队,在汤恩伯、阎锡山的疯狂“围剿”下,被迫转入地下,在霍县铁路线上、东山伐木区等地活动。红军河东抗日游击支队指导员刘占江也化名石圪垯,在东山一家伐木厂当了伐木工人。
这天,有人给刘占江捎来口信,是支队政治部主任张国华在返回陕北前留下的话,要他设法速回陕北。
可敌人在汾河、吕梁山、黄河东岸布下了三道封锁线。乌龟壳似的碉堡,密布在封锁线上,五里一大堡,三里一小碉,什么子母堡、梅花碉,花样繁多。要重返陕北,谈何容易啊!
但尽快返回陕北的信念不容刘占江有丝毫退缩的念头,而且红军东征这几个月来在这里打下的群众基础,也让他坚信自己一定能闯过敌人的道道关卡。于是在秋末的一天,刘占江离开伐木厂,开始了重返陕北的征程。
刘占江穿着一件破旧的蓝粗布棉袄,白老布裤子,头上包着一条肮脏的毛巾,装成一个从山里出来到平川地寻活儿干的穷苦农民,沿着大路向霍县城走去。霍县城在汾河边上,是他要经过的第一道“关口”。
从东山到霍县东门,40多里路,刘占江下半夜起身,一清早就走到了。远远地,霍县城高大的城门已经看得分明,城门口站着4个岗哨:两个汤恩伯的“正规军”,两个阎锡山的“公安队”。
刘占江悄悄地观察了一下,看见岗哨们贼眉鼠眼地盯着过往的行人,不时大声吆喝着。他们对那些认为形迹可疑的人,全身上下进行搜查。刘占江迟疑了一阵,便鼓起勇气不慌不忙地向城门走去。
已经越过哨位,进到门洞里了,刘占江刚松了一口气,忽听身后一声大喊:“那个老百姓,站住!”他装着没听见,头也不回只顾走着。“站住!”后面响起了拉枪栓的声音和追赶的脚步声。
刘占江只好停下来,扭过头,一个“公安队”队员已经狠狠地抓住了他的衣领,拿阴沉沉的眼光瞅着他说:“怎么,你是聋子?”“噢!老总,你是叫我?”他装着莫名其妙的样子,怯生生地回人的话。
“别装蒜!”刘占江被推到城门口,进行搜查。敌人从他裤腰带里搜出了两个钢洋,这是他好不容易才凑起来的全部路费。当着“正规军”的面,“公安队”不敢把钢洋揣进自己的腰包里,但也不肯放过刘占江。
“公安队”气势汹汹地盘问:“你是干什么的?”刘占江刚要答话,敌人就狠狠地用皮带照他脸上抽了两下:“你是土匪,跟上红军抢来的!”
刘占江强压住心里的愤怒说:“老总,我是好老百姓,这钢洋是帮人干活挣来的钱,一年的辛苦啊!还给我吧。”“公安队”得意地笑着说:“还你?没那么容易,蹲大牢去!你是土匪,钢洋是证据!”
不容刘占江再解释,两个“公安队”队员,端起上着明晃晃刺刀的枪,把刘占江押送到了城里的监狱。刘占江心里暗自着急,才开始走第一步,就进了监狱,这可怎么回陕北啊。
随着铁门沉重的响声,刘占江被关了起来,顿时听见镣铐相碰的“当啷”声和被拷问过的犯人的痛苦呻吟声。牢房里没有窗户,阴暗得很,刘占江摸索着靠墙坐下,好一阵儿才看清周围的一切。
牢房内已有十几个和他一样的农民,他们面黄肌瘦,衣衫褴褛,用同情的眼光向刘占江问询。在没弄清他们是什么人以前,刘占江知道自己不能多说话。只是垂下头,避开他们的眼光。
牢房里很阴森,潮湿的土地上铺着几根谷草。臭虫、跳蚤已经开始在刘占江的腿上叮咬起来。被子被岗哨丢在城门口了,刘占江只好紧抱双膝坐着,心里不住地翻腾,计划着怎样应付审讯。
刘占江知道,决不能说出自己工作过的那个伐木厂,因为那里还有好些同志,也有人知道他的真正身份。如果敌人去查对,自己和同志们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。但是该怎样骗过敌人呢?
刘占江,一个刚刚19岁的红军指导员,吃过苦,打过仗,挂过彩,可蹲牢还是头一次。一想到这里,他的心里不由得有些凌乱。寒冷和饥饿也一起袭来,他困得慢慢地合上了眼皮。
迷糊中,忽然有人在他耳边低声说:“是刘指导员吗?”刘占江猛地一惊,愣了愣,没有答理。那人更小声地说:“我认得你,你怎么被抓到这地方来了啊?”那颤抖的声音,充满了同情和关切,刘占江不由得扭过脸去。
借着一点微光,刘占江看见那是一位年老的农民,面孔是很熟,但他还是机警地回答:“大伯,我不懂你的话,我叫石圪垯,东山里的庄稼人。”老人呆了一阵子,点点头说:“不懂也好,可要小心啊!”便再不吭声了。
刘占江的睡意被赶跑了,心里想,这老汉是谁呢?他又偷偷地看了老人半天,终于想起来了,是李信,李大伯。他们连曾在老人家中住过,李大伯可是个善良的农民,待红军好比亲骨肉,怎么他也坐牢呢?刘占江决定探问一下。
刘占江往李大伯身边凑了凑,咬着耳朵问:“大伯,你怎么也到这地方来了?”李大伯见刘占江问,便说:“是拉下饥荒被抓来的。”他叹了口气,说:“唉!想起你们闹得红火那阵,咱穷人多有指望,如今,刀又架上脖子了!”
刘占江的心完全放下了,便把自己被捕的经过告诉了他。李大伯用枯柴棒子般的凉手握着刘占江的手说:“得想个法子出去。”不多一会儿,牢外看守高声喊叫:“今天的犯人下午过堂。”
时间迫近了,要想出妥当的办法。刘占江看了看李大伯,老人猛地直起腰,搂住刘占江的肩膀,咬着耳朵说:“我舍命也要救你出去。我60多岁的人了,能救得你,死也闭眼。你出去还能救无数受苦的人啊。”
李大伯想了想,问刘占江:“你在小水玉庄住过吗?”刘占江点点头。他又说:“白兰芳你认识吗?他是我同乡,都是从河南逃荒出来的,你就说是他伙计,两块钢洋是他给的工钱。他们要不信,你就提我的名字,我给你担保。”
“石圪垯,过堂!”过了一会儿,门外响起看守冷冰冰的叫声,铁门响起了开锁的声音,难友们都无声地看着刘占江,替他担心。
刘占江被两个“公安队”队员连推带踢地押上法庭。阎锡山的衙门,封建劲头十足,当堂挂着两根碗口粗的大绳,还有扁担、杠子、水桶、火钎…………两边还站着几个打手,让人一踏进门槛就感到一股阴森森的气氛。
大堂上坐着霍县公安局局长,一个像棍子一般细长的大烟鬼。他面色铁青,红黑不问,先向打手摆了摆头说:“打!”“噼噼啪啪”,刘占江的手掌挨了几十竹板。
打完后,公安局长把两块钢洋晃了晃,问道:“石圪垯,实说,抢哪一家的?”他狞笑着,露出被大烟熏得乌黑的牙齿。刘占江按照想好的话,结结巴巴地说了,还说在牢里碰上同村的李大伯,可以证明自己是良民。
公安局长见审不出破绽,恼羞成怒地大吼一声,又把头一摆,立时刘占江就被几个人用棍子打倒在地上,头上手上流出鲜血。他勉强从地上站起,腥咸的血一直流到嘴里,他舔着嘴唇,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。
法庭沉寂了一阵,忽然门外有人喊:“走!不说实话,要你的老命!”是李大伯来了,刘占江的心“咚咚”地跳起来。李大伯被捆到堂上,显然他们已经威吓过他了。李大伯颤巍巍地站在刘占江身边,不断喘气呻吟。
在大堂明亮的灯光下,刘占江才看清,李大伯比过去苍老多了,花白的胡子上,沾着口水。公安局长问他话后,他很熟识地向刘占江望了望,回答说:“他吗?我认得的。他是俺同乡白兰芳的伙计,是个老诚忠厚的人。”
公安局长把两块钢洋在桌上使劲地敲了几下,说:“他不抢人,这钢洋哪儿来的?”李大伯眯起眼,故意端详他手中的钢洋,回答说:“长官,这别疑惑,我知道这两块钢洋是石圪垯一年的辛苦,他这人啊..”
公安局长像疯子似的吼道:“李信,你敢担保吗?包庇红军、土匪,一样人头落地!”李大伯镇定地说:“长官,我60多岁的人了,还撒什么谎,我敢担保!”
第二天,天刚亮,就听见看守冷冰冰的声音在门外喊:“石圪垯,放你出去了。”刘占江转身抱住李大伯,热泪夺眶而出。只听李大伯说:“娃儿,走吧!我要是不死,总有一天,还能看见你们!”微弱的光线里,刘占江看到他的眼角也噙着两颗晶莹的泪珠。
虽然脱险了,但没了路费,继续往陕北走也不可能了。没有办法,刘占江又转回了东山。为了能赚些钱当路费,刘占江的伤好以后,便在拖板沟村一家伐木厂干活。

在伐木厂,刘占江结识了工人王师傅,和他成了知心朋友。一天,王师傅突然很神秘地悄悄说:“兄弟,我知道你是干啥的。咱们是一根蔓上的苦瓜果,早晚扔进一个筐里。红军是工人阶级的队伍,这我了解。”
刘占江看他很可靠,就半露不露地讲了几句含糊的话。试探地问能不能帮他回陕北去。王师傅把胸脯一挺,用粗大的手压着刘占江的肩说:“好吧。你先干几天,我慢慢想个办法。你知道,想过卡子非弄个证明不行!”
一天晚上,刘占江因扛了一天木板,又累又困,天刚黑,就倒在木屋里想睡觉。王师傅满脸高兴地走进屋来,拉住刘占江说:“起来!”他把嘴挨着刘占江耳朵说:“我送你回陕北。”
一听这话,刘占江一下子翻身从地上坐起来。他知道王师傅是直性子人,说一不二,可是事情真有这么快?刘占江拿猜疑的眼光望着他。只见王师傅从腰里掏出一张纸片,是由霍县到黄河边石楼县的通行证。
“明天一早就动身,都安排妥帖了。”王师傅说。刘占江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,好一阵才从嘴里吐出几个字:“好王师傅,怎么报答你呢?”王师傅咧开嘴笑着说:“这算得了什么。”
王师傅端来两大碗菜,一碗是野兔子肉,一碗是野素杂烩。这是他抽空从山林子里采出来的,猴头、蘑菇、地衣、野黄花、山蒜薹等等,这在东山伐木区算是最上等的吃食了。“怎么,这样好的饭菜?”刘占江不安地说。
吃吧!兄弟,咱可不是吃人血汗,是自己弄来的。”说着,王师傅又从怀里掏出足有2斤重的一块白面饼子,把大半个塞在刘占江手里。在山里,成年累月吃的都是苦荞面、谷子饭、山药蛋,白面一年也吃不上一次的。
下半夜,山里刮起大风,松涛声像黄河的波涛一样吼叫着。近处树林里,野鹿受不住寒冷,凄厉地号叫。王师傅很快穿好了衣服,起来点着了旱烟锅,把木匠工具结扎停当,说:“走!早走一袋烟,少赶三十三。”
走了30多里,天渐渐放明,他们来到汾河封锁线的一个关口。这里岗哨密布,碉堡林立,行人都要遭到严密的检查盘问。王师傅在前头,刘占江跟在后面,两人都拿着木匠工具,一看就是师徒俩。
关口上站着汤恩伯的“正规军”和“防共保卫团”的地主武装。刘占江二人一走上去,就被围住了。一个头领模样的人横眉竖眼地问:“你们是干什么的?”王师傅泰然地说:“我们是手艺人。”
那人把老王上下打量了一阵,又龇牙咧嘴地威吓:“手艺人也不准过,阎主席的命令,违抗的就这个···”他把手在自己脖子上一拭。老王慢慢从腰里掏出通行证:“老总,正是他老人家叫我俩到黄河边修碉堡呀!这年头,谁想跑这远路呀··”
那人一把抢过通行证,看了两眼,规规矩矩地递给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。那家伙点了点头,把通行证交还给王师傅说:“去吧!好好修。”连身上都没搜查,便把刘占江他们放过去了。
刘占江他们大摇大摆地过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。用同样的方法,他们又越过了吕梁山的乔家(墕)第二道封锁线,走到黄河边上的石楼县地区。这里碉堡密得像围棋盘上的棋子,防守更是分外严密。
刘占江对王师傅说:“山核桃剥了皮,就剩一层蒙子了。”王师傅有些愁闷地说:“这层蒙子可就不那么好剥了,咱们的证明到河边就不生效了。”这里,黄河把东西分成两个世界,刀砍斧劈的峭壁下,河水像千军万马吼喊着向东南奔流。
初冬时分,黄河水已带着冰凌,不能渡船,河水也寒气森森,令人心惊胆战。刘占江站在东岸遥望陕北,恨不得飞过黄河去。但这最后一道难关挡住了他返回陕北的步伐。
一时过不了河,他们便在离河边60里的后河村刘生业老汉家住下来。因为同姓刘,刘占江便叫他刘大伯。黄河边上,阎锡山的部队成天穿梭巡查,挨户搜索,闹得鸡飞狗跳墙,而刘大伯家离黄河较远,比较安全。
刘大伯是陕北清涧人,和刘占江老家只隔一个村子,所以两人拉扯得很亲热。每天,王师傅扛上木匠工具在邻近村子转着找零活,掩护身份;刘占江就在刘大伯家做活儿,给他当伙计。因为他们是乡亲,所以也没人怀疑。
一次,刘占江试着向刘大伯谈起回陕北的意思,刘大伯很恐惧地说:“困难啊,如今是隔河相望,黄河好比阴阳界了。”随后他又想了一阵,说:“老乡,别着急,先住上段日子,我慢慢想法子。”
一天,老王在邻村做活儿,遭到了阎军的盘查。虽然被他应付了过去,但已引起敌人的怀疑,村长三番五次到刘大伯家来打听刘占江他们是什么人。“防共保卫团”就驻在离这儿十来里,如果突然闯来盘查,问题就严重了。
夜里,王师傅把刘占江叫到围墙背后,搂住刘占江的肩膀,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:“兄弟,风声紧得很,我又不能送你过河,想回去了,咱们不能让敌人一网打尽。”
刘占江听了,忍不住哭了起来,眼泪止不住地在脸上流淌。好一阵,王师傅才挣脱刘占江的手说:“我走了,代我多谢刘老汉。盼你们快点打过来!”说完他紧了紧腰带,提起放在地上的木匠工具,大步地向来路走去。
刘占江呆愣愣地站在那里,直视着他高大的身影渐渐被夜色吞没,心里默默地祝福他平平安安地回到东山。
隔天一早,刘占江起床时,刘大伯已经出门了。晚上他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,向刘占江说:“今天白跑了一趟。你不要慌,我会给你想办法的。”刘占江望着大伯,也不好再多问什么。
第二天,刘大伯的儿子告诉刘占江,刘大伯为了帮刘占江回陕北,把家里准备过年烧的柴卖掉,买了一瓶好酒,割了5斤猪肉,跑到村长家,想找他替刘占江活动过河的证照。谁想黑心的村长收了礼却不办事。
冬天已经来临,黄河边上的寒风,成天呼啸。隔河遥望陕北的山峦、村落、树丛,刘占江心里急得真像热锅上的蚂蚁,但他不识水性,不能独自凫水过河,只能边在刘大伯家帮助做些零活边打听过河的办法。
有一天,刘大伯又一早就出门去了。晚上,他回到家里,满脸笑容,腋下挟着一包东西,一见刘占江就乐滋滋地说:“娃儿,算想了个法子,虽是风险些,就此一条路了。”
刘大伯话音未落,门外又跨进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,那人长得很结实,猛一看有一股威武的劲头。刘大伯介绍说:“娃,这是殷大叔,黄河上的老手,走河路20多年了,他答应运你过黄河。”
这个不爱说话的老水手,眼睛看着烟锅里的火星子,慢吞吞地说:“我琢磨了好久,咱们从义碟区小河汊过河,那里水急,可是他们防守也比较松些。那里崖坎石沟、七里八湾,老茅草一人多高,碰上巡查队也有个躲藏。”
刘占江往他跟前凑了凑问:“大叔,你以往干过这号事吗?”“好多回了,送过贩私盐的,还有红军。”说到“红军”两个字时,他用眼光瞅了瞅刘占江。刘占江没有回答,不用说,彼此心里都明白。
这时候,刘大伯打开包袱,取出一身里外光板的老羊皮衣,对刘占江说:“到河边,把这换上,要不过了河,就成冰棍子哩。”刘占江感激地接在手里。
刘大伯特意做了一锅汤面,还蒸了几个米面馍,一碗羊肉炖萝卜,一碗腌酸菜,像是给刘占江送行。他今天比往常快乐,不断地劝刘占江多吃,还弄来一小瓶烧酒,和老水手喝了几盅。
想到马上就要偷渡,刘占江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地直翻腾,可他看见老水手慢慢地喝着酒,吃着菜,一点也不慌张。这使刘占江想起了王师傅,觉得他们有些地方很是相像。
动身的时间到了。刘大伯送了他们几里路,刘占江劝他回去,他硬要送到河边,刘占江犟不过他。又走了几里,刘占江说:“大伯,回去吧,迟早都要分手。往后,我定来看你。”老水手也说:“回去吧,你放心,有我在。”
刘大伯站住脚,握住刘占江的手,泪花花地说:“好吧,娃,我回去了唉!我是‘身在曹营心在汉’,没有一天忘记红了的老家。你要能到清涧,一定要到我老汉家去一趟···”刘占江说:“大伯,我都记住了,你放心。”
刘大伯想了一阵,又说:“娃,你要是到了延安府,代老汉问候毛主席一声,就说河东的老百姓,日子过得凄惨,盼他老人家带领人马再东渡黄河来搭救。”刘占江攥着拳,肯定地说:“大伯,那日子没多久啦!”
老水手在前领路,高一脚,低一脚,快步往河边飞奔,下半夜他们便到了小河汊。这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和黄河成丁字形的岔口。在陡峭的沟峪里,有一股不大的水流入黄河。
他们在离黄河还有五六里的地方,就顺着之字形的打樵路,下到沟底,然后沿着小河走向黄河边。因为这里黄河两岸是百丈悬崖,很难下去,而且河边上碉堡一个紧挨一个,敌人看守得最紧,日夜在河边巡逻。
河汊的深沟里,乱石峥嵘,长满了锐利的狼牙刺和半人多高的茅草。路很难走,老水手很熟悉地拨开乱草为刘占江开路。刘占江背着一个很轻巧的羊皮筏子,紧跟在后面,跌跌绊绊地走着,心里又兴奋又紧张。
黄河越来越近,在寂静的深夜,奔腾的吼声听得很真。要没什么意外,不用一个小时,就可以到河西啦!就在这时,走在前面的老水手猛地站定,转身把刘占江肩头一按,说:“有人!”两人便连忙弓腰闪进一个石崖缝里。

谁知,一不小心,刘占江把一块石头蹬进水坑里,发出一阵“噗噜噜”的声响。这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,觉得比打雷还要响,刘占江紧张得呼吸都快停止了。
沟沿上,敌人的脚步声突然停住,他们正站在刘占江他们头上四五丈高的地方。敌人的手电筒雪亮的光芒,在他们眼前乱晃,幸好他们躲在阴影里紧贴着崖壁,和敌人几乎上下一条直线,电光照射不到。
刘占江清楚地听见一个敌人用慌张的声音对另一个说:“听见没有,沟里有动静。”另一个人回答:“好像什么东西滚进水里。”“是不是下去瞧瞧?”
糟了!敌人要下到沟里,那就碰上了。刘占江弯腰从地上轻轻拣起一个石块,准备敌人下来就跟他们拼了。老水手看见了,急得直拉刘占江的衣角。
这时,沟沿上另一个敌人开腔了:“别下去了,路也没有,全是乱石茅草。”手电的光又在他们面前一两米远的地方晃动,差一点照到羊皮筏子上。过了一会儿,一个敌人说:“没什么,走!到前面村里烤火去!”
巡逻队凌乱的脚步声远了,他们是从南往北,和刘占江他们走相反的路。又等了一阵,老水手才拉着刘占江的手说:“真险,走!”
出河汊到黄河边上了,虽说抬头就可以看见高崖上敌人碉堡枪眼里射出的灯光,但危险性却小得多了。高崖的暗影,几乎遮着整个河面,河水的吼声也掩盖了一切声响。
刘占江他们从容地换上皮衣皮裤,老水手轻轻把筏子推进水中,两人跳上去坐定。急浪一眨眼就把羊皮筏子打了几丈远。
筏子随着波浪,一起一落,冰凌撞着筏子,发出“嚓啦嚓啦”的声响。有时一个大浪,把小得可怜的筏子涌起丈把高,人好像腾在半空。刘占江紧紧地抓着支架,老水手避开漩涡、急浪,熟练地和河水搏斗。
刘占江回头看东岸,碉堡的枪眼里,闪着鬼火似的光,好像一些狡猾的眼睛瞅着他们。西岸,看不见灯火,静悄悄的河沿上,几棵大树干在夜空中倔强地挺立着,虽然什么也看不清,但想着马上能回到陕北了刘占江心里也暖丝丝的。
靠岸了,老水手立刻向刘占江告别:“兄弟!好了,我要赶在天亮前回去。”刘占江紧紧拉着他的手说:“不喘口气吗?”他平淡地一笑:“不是时候,见面的机会有的是,我这一辈子都在黄河上。说不定还能接你过河东!”
刘占江激动得举起手向他敬了个军礼,说:“向您敬一个红军的礼,代我问候刘大伯,我不会忘记他的。”老水手把手在头上一比画:“我们盼着打过黄河的红军!”说毕,他把筏子推进水里,跃身而上,筏子划向了西岸。
刘占江迅速爬上羊肠盘道走上河沿,站在河沿上,他长久地望着河东,李大伯、王师傅、刘大伯、殷大叔,好多河东人民熟悉的面孔,又出现在他眼前。他知道,应该怎样工作、战斗,才对得起河东的乡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