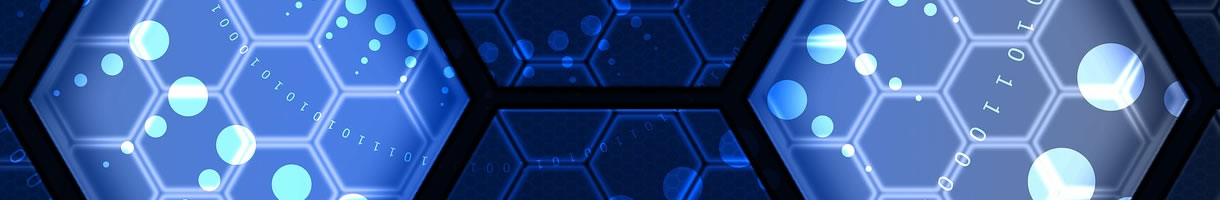695年,72岁的武则天召33岁的薛怀义共度良宵,薛怀义兴奋奔往寝宫,武则天却下令:“把他给朕抓住!”
声明:本篇故事为虚构内容,如有雷同纯属巧合,采用文学创作手法,融合历史传说与民间故事元素。故事中的人物对话、情节发展均为虚构创作,不代表真实历史事件。

神都洛阳,证圣元年,公元695年。这座被权力与欲望浸透的都城,在一位空前绝后的女皇帝治下,正经历着它最辉煌也最诡谲的时代。夜幕如一张巨大的黑丝绒,将巍峨的宫殿群笼罩,唯有明堂顶端的巨大凤鸟,在月光下折射出冰冷的金属光泽,俯瞰着芸芸众生。
这一年,女皇武则天七十二岁,岁月的风霜早已刻上她的额头,但那双凤目中的威严与深沉,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不敢直视。而三十三岁的薛怀义,正值壮年,手握权柄,圣眷正浓,是洛阳城里最炙手可热的人物。
当一纸来自女皇寝宫的密诏,召他共度良宵时,他以为这不过是又一个缠绵缱绻的夜晚,是女皇对他无上宠爱的又一次证明。
他满心欢喜,甚至带着几分炫耀的得意,奔向那座权力的巅峰,却不知,等待他的,不是温香软玉的龙床,而是一道冰冷彻骨的圣旨:“把他给朕抓住!”
“陛下,夜深了,是否要歇息了?”上官婉儿轻移莲步,将一盏新烹的安神茶放在案头,声音轻柔得如同拂过殿角的晚风。
武则天没有回头,她的目光依旧凝视着窗外那片沉沉的夜色,夜色尽头,是万象神宫冲天的废墟轮廓,像一道丑陋的伤疤,烙印在神都的夜空,也烙印在她的心头。“婉儿,你说,人心,究竟能膨胀到何种地步?”她的声音有些沙哑,听不出喜怒,却带着一股令人心悸的疲惫。
上官婉儿心中一凛,她知道陛下问的是谁。除了那个凭借圣眷而无法无天的薛怀义,还能有谁?她垂下眼帘,谨慎地回答:“人心如水,可载舟,亦可覆舟。无堤坝束之,则泛滥成灾。”
“好一个泛滥成灾。”武则天缓缓转过身,案上的烛火跳动着,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影。“朕给了他别人几辈子都求不来的富贵荣华,让他从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,成了统领万军的大将军,敕封鄂国公。朕甚至……容忍了他的一切骄横跋扈。可他回报给朕的,就是一把火,烧了朕的万象神宫,烧了朕昭告天命的神圣殿堂。”
她的话语很平静,但上官婉儿却听出那平静之下压抑的雷霆之怒。那场大火已经过去数日,整个洛阳城都在谈论着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官方的说法是役夫夜间作业不慎,引燃了天堂,最终殃及明堂。但宫中稍有地位的人都心知肚明,那把火,正是薛怀义在一场争风吃醋的妒火中烧之下,亲手点燃的。
“陛下息怒,龙体为重。”上官婉儿跪倒在地,“薛大将军或许只是一时糊涂,被嫉妒蒙蔽了心智……”
“糊涂?”武则天冷笑一声,那笑声在空旷的大殿里显得格外刺耳。“他不是糊涂,他是狂妄。他以为朕对他的那点情分,可以让他为所欲为,可以让他挑战朕的底线。他以为这大周的江山,他也有份么?他忘了,他的一切,都是朕给的。朕能给他,自然也能收回来。”
上官婉儿伏在地上,不敢再多言。她见证了薛怀义的崛起,也预感到了他的覆灭。这个原名冯小宝的男人,本是洛阳城里一个靠贩卖草药为生的小货郎,生得一副高大魁梧的好皮囊,又能说会道,颇有几分市井的机灵。机缘巧合之下,他被千金公主府上的一名侍女看中,两人私通,后被公主发现。千金公主见他体格健壮,样貌不凡,又正愁如何讨好孀居的武则天,便心生一计,将他沐浴更衣,献给了当时还是太后的武则天。
那时的武则天,刚刚失去次子李贤,长子李弘也早已不在人世,政治上的压力和内心的孤独让她身心俱疲。冯小宝的出现,如同一股粗野而充满生命力的狂风,吹进了她压抑沉闷的后宫生活。他不像宫中那些唯唯诺诺的宦官,也不像朝堂上那些心思深沉的大臣。他直接、热情,带着一股原始的野性,恰好填补了武则天情感上的空缺。
为了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,武则天让他削发为僧,改名“怀义”,并任命他为白马寺的主持。为了方便他出入宫禁,又让他认自己的女婿,也就是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为季父,改姓薛。从此,冯小宝就成了薛怀义,一个可以随时随地出入皇宫的“薛师”。
武则天对他的宠爱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她知道薛怀义出身低微,恐被人瞧不起,便不断地为他加官进爵。她要建明堂,一座象征她无上权威、沟通天地的神圣建筑,便让薛怀义担任督造。薛怀义虽不懂营造之法,却精力旺盛,善于驱使役夫,硬是让这座规模宏大、极尽奢华的建筑在极短的时间内拔地而起。明堂建成,高二百九十四尺,方三百尺,共分三层,气势恢宏,天下为之震动。武则天大悦,拜薛怀义为左威卫大将军,封梁国公。
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,武则天需要为自己“女主临朝”找到理论依据。薛怀义又投其所好,网罗了一批僧人,伪造了一部《大云经》,宣称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,当代替李唐君临天下。这部经书的出现,为武则天登基称帝铺平了道路,其政治意义无可估量。武则天龙颜大悦,再次加封他为辅国大将军、鄂国公,权势一时无两。
手握军权,身负皇恩,薛怀义的野心和欲望也随之急剧膨胀。他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女皇的伴侣,他开始渴望真正的权力。他出入乘坐御赐的马匹,随从动辄数百人,皆是剃光了头的市井无赖和亡命之徒,号称“净众”。这支队伍在洛阳城中横行霸道,殴打官吏,抢掠商铺,百姓怨声载道,却无人敢管。
一次,薛怀义在路上遇到了时任右台御史大夫的冯思勖,因其没有及时避让,竟命手下将其拖下马,打得半死。朝中百官,无不侧目,却敢怒不敢言。更有甚者,一次他与宰相苏良嗣在朝堂门口相遇,因道路狭窄,薛怀义仗着自己是“国师”,便要苏良嗣让路。苏良嗣为人刚正不阿,哪里会将这个幸进之徒放在眼里,冷冷地说道:“各走各道,何来让路之说?”
薛怀义自觉受辱,竟当着文武百官的面,对这位年过花甲的宰相拳打脚踢。苏良嗣没有还手,只是在薛怀义打累了之后,掸了掸官袍上的灰尘,平静地对他说:“我苏良嗣,手能执笔安天下,不能与你这等小人搏斗。”说完,昂首走入殿中。
这件事传到了武则天的耳朵里。她将苏良嗣召来,温言抚慰,并赏赐了许多财物。但对于薛怀义,她却只是轻描淡写地斥责了几句。她对苏良嗣说:“宰相是国之栋梁,朕知你受了委屈。但薛师于国有功,又是方外之人,爱卿还需多担待。”
这看似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方式,实际上却是对薛怀易的纵容。这种纵容,让薛怀义的胆子越来越大。他开始公然在自己的府邸里剃度了上千名僧人,名为弘扬佛法,实为蓄养私人武装。他甚至在北门公开悬挂自己的巨幅画像,其用心昭然若揭。
武则天并非昏聩之人,她将薛怀义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。但起初,她选择了容忍。一方面,薛怀义在她登基的过程中确实立下过汗马功劳,是她一手扶持起来的政治符号;另一方面,多年的情分,让她对他总有几分不舍。她以为,只要自己稍加敲打,这个男人就会收敛。
然而,她低估了权力和欲望对一个人的腐蚀速度。随着武则天年事已高,她开始寻求新的慰藉。一个名叫沈南璆的御医,因其温文尔雅、博学多才,且善于养生之道,逐渐获得了女皇的青睐。与粗野狂放的薛怀义不同,沈南璆能陪着武则天谈论诗文,探讨道法,他的存在,更像是一个精神上的伴侣。
宫中的风向变得很快。曾经只为薛怀义一人敞开的寝宫,如今沈南璆也能自由出入。曾经只属于薛怀义的温存和笑语,如今更多地给予了那个文弱的御医。薛怀义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,他那颗被嫉妒和占有欲填满的心,开始扭曲变形。
他开始变得喜怒无常,时常在宫门外大吵大闹,指名道姓地要见女皇。武则天对他日益增长的骄横感到厌烦,多次拒而不见。这种冷遇,更是火上浇油。薛怀义的怨气与日俱增,他将这一切都归咎于沈南璆,认为是这个“小白脸”抢走了本该属于他的一切。
终于,在那个改变了他命运的夜晚,薛怀义在酒后再次前往皇宫求见,却被宦官拦在了宫门之外,理由是“陛下已经歇息”。而他透过门缝,隐约看到沈南璆的身影在殿内的烛光下晃动。这一下,彻底点燃了他心中的炸药桶。
“好你个武媚!我为你出生入死,为你建明堂,为你造《大云经》,你就是这么对我的?”他在宫门外疯狂地咆哮,声音嘶哑而绝望,“你宁可选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医生,也不见我?我得不到的,别人也休想得到!”

一股毁灭的欲望冲昏了他的头脑。他看着不远处在夜色中巍峨耸立的万象神宫,那座由他亲手督造的建筑,是他功勋的顶峰,也是他荣耀的象征。但此刻,在他眼中,那却成了对他最大的讽刺。他要毁了它,毁了这座女皇最珍视的殿堂,让她知道,他薛怀义,不是可以随意丢弃的玩物!
他带着几个心腹,绕到了神宫的北侧。那里是高达百尺的“天堂”,一座用来存放巨大佛像的木塔。他红着眼睛,状若疯魔,亲手将火把扔进了堆放木料和麻布的角落。
干燥的木材遇到烈火,瞬间熊熊燃烧起来。火借风势,风助火威,不过一刻钟的功夫,整座天堂就被大火吞噬。火舌冲天而起,高达数百尺,将半个洛阳城都照得亮如白昼。天堂巨大的木结构在烈火中噼啪作响,不断发出令人牙酸的断裂声,最终轰然倒塌。无数燃烧的木块和火星,如同流星雨一般,飞溅到紧邻的明堂之上。
明堂,这座象征着大周皇朝天命所归的建筑,也随之陷入了一片火海。当武则天被惊醒,登上宫城的最高处时,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末日般的景象。她亲手缔造的辉煌,她引以为傲的功绩,正在她眼前化为灰烬。
她没有哭,也没有怒吼。她只是静静地站着,任凭凛冽的夜风吹拂着她花白的头发。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,但那双凤目中,却燃烧着比那场大火更加炽热、也更加冰冷的火焰。上官婉儿站在她的身后,能清晰地感受到从女皇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彻骨的寒意。她知道,薛怀义的死期到了。
大火过后,洛阳城一片狼藉。明堂和天堂被烧成了一片焦黑的废墟,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,在风中发出呜咽。朝野震动,人心惶惶。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薛怀义的报复之举,但没有人敢公开说出来。武则天出人意料地没有追查此事,只是下令将此事定性为意外,并宣布要择日重建明堂,而且要比原来的更加宏伟壮丽。
对于薛怀义,她更是一反常态地表现出了宽容。她派人传话给他,说自己知道他并非有意,只是一时冲动,她并不怪罪他。她甚至还赏赐了他许多金银财宝,以示安抚。
薛怀义本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,甚至想过要不要集结他手下的那批“净众”作乱。但武则天的这番表态,让他紧绷的神经瞬间松懈了下来。他那被宠坏了的头脑,再一次被自负和幻想所占据。他想:“她还是舍不得我的。她心里还是有我的。烧了明堂又如何?只要她还爱我,我薛怀义就永远不会倒。”
他开始相信,这不过是他们之间的一次争吵,一次闹得比较大的别扭。只要他服个软,认个错,女皇就会像以前一样,重新将他拥入怀中。他甚至觉得,这次大火,反而证明了他在女皇心中的分量。
于是,他开始频繁地派人给武则天送去各种礼物,写一些情意绵绵的信,请求她的原谅。而武则天也一一收下,并且回信的语气也越来越温和。一切似乎都在朝着薛怀义期望的方向发展。
终于,在几天后的一个黄昏,薛怀义等来了他梦寐以求的消息。一名宫中的小黄门,带着女皇的亲笔密诏,来到了他的府邸。密诏上的内容很简单,只有寥寥数语,却让薛怀义欣喜若狂。
“朕已知汝悔过之心。今夜子时,来瑶光殿,朕与你重归于好。”
瑶光殿,那是宫中一处较为偏僻的宫殿,是他们早年经常私会的地方。这个地点的选择,更让薛怀义坚信,女皇是要与他和好如初,并且不想让外人知道,以免落人口实。
他激动得浑身颤抖,立刻命人取来自己最华丽的衣服,精心打扮起来。他对着镜子,看着自己依旧英武的面庞和强健的体魄,充满了自信。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女皇含情脉脉的眼神,已经感受到了那熟悉的温存。他甚至在心里盘算着,今夜一定要好好表现,让女皇知道,他薛怀义,才是那个最能让她满足的男人,那个沈南璆,不过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药罐子。
他屏退了所有的随从,因为密诏上特意嘱咐,让他一人前来。这在他看来,更是女皇体贴入微的表现。夜色渐深,他骑上一匹快马,独自一人,怀着无比兴奋和期待的心情,朝着皇宫的方向疾驰而去。洛阳城的街道在他身后远去,巍峨的宫墙越来越近。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重新走上权力巅峰的辉煌未来。他心中充满了得意与轻蔑:“烧了一座明堂算什么?只要这个女人离不开我,整个天下迟早都是我的!”
他顺利地通过了宫门,卫兵们似乎早已得到了命令,对他视若无睹。他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了瑶光殿前。殿内透出温暖的灯光,一切都显得那么静谧而美好。他整理了一下衣冠,深吸一口气,推开了那扇沉重的殿门。
殿内的陈设和他记忆中一样,香炉里焚着他熟悉的龙涎香。然而,殿中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龙床凤帐,也没有等待着他的女皇。空旷的大殿中央,站着几个人。为首的,是武则天的侄子,建昌王武攸宁,他的身后,是十几个身材魁梧、手持棍棒的壮汉,一个个面色不善,眼神冰冷。
薛怀义的心猛地一沉,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了他。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,厉声问道:“武攸宁?你在这里做什么?陛下呢?!”
武攸宁看着他,脸上露出一丝怜悯又夹杂着快意的冷笑。“薛师,别来无恙啊。陛下自然在等您,只不过,不是在这里。”

“什么意思?”薛怀义警惕地后退一步,手已经摸向了腰间的短刀。
就在这时,从大殿的屏风后面,传来了一个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。那是武则天的声音,却不带一丝一毫的温度,冰冷得如同数九寒冬的玄冰,穿透了殿宇,也穿透了薛怀义的耳膜。
那声音威严而冷酷,不容置疑,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毒的利刃,狠狠地扎进薛怀义的心脏:“薛怀义骄狂无状,罪不容诛。今火烧神宫,更是悖逆滔天!武攸宁,还不与朕将这逆贼拿下!”
命令下达的瞬间,薛怀义脸上的血色褪尽,兴奋与期待在刹那间化为彻骨的寒意与惊恐。
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那个曾对他柔情蜜意的女人,那个他以为永远能掌控于股掌之间的女皇,竟然真的对他动了杀心!瑶光殿的大门在他身后“砰”的一声轰然关闭,断绝了他所有的退路。
“不!陛下!陛下!是我!是怀义啊!”薛怀义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,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。他猛地转身,想去拉开那扇紧闭的大门,但为时已晚。武攸宁一挥手,那十几个壮汉如同饿狼扑食一般,手持沉重的枣木棍,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。
“武媚!你这个毒妇!你骗我!”薛怀义彻底疯狂了,他拔出腰间的短刀,眼中迸发出困兽犹斗的凶光。他毕竟是行伍出身,身手远非常人可比。面对围攻,他不退反进,手中的短刀上下翻飞,划出一道道致命的寒光。最先冲上来的两名壮汉躲闪不及,惨叫着倒在血泊之中。
“结阵!给我打!”武攸宁脸色一变,厉声喝道。他没想到薛怀义竟如此悍勇,急忙后退几步,躲到柱子后面。
剩下的壮汉们显然是经过特殊训练的死士,他们不再各自为战,而是迅速组成了一个简单的合围阵型。他们手中的棍棒不再是胡乱挥舞,而是变得极有章法,专门朝着薛怀义的下盘和关节处招呼。薛怀义虽然勇猛,但双拳难敌四手,更何况对方人多势众,兵器又是长兵。他手中的短刀在格挡了几下沉重的棍击后,虎口便被震得鲜血淋漓,几乎握持不住。
“砰!”一根木棍狠狠地砸在他的左腿膝盖上,他闷哼一声,单膝跪倒在地。瞬间,无数的棍棒如同雨点般落在了他的背上、头上、四肢上。他感觉自己的骨头仿佛一寸寸地断裂,剧痛传遍全身。
“啊——!武则天!你出来!你亲口对我说!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!”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嘶吼着,声音里充满了不甘、怨恨和一丝残存的乞求。他仍然幻想着,只要女皇听到他的声音,或许会心软,会改变主意。
然而,回答他的,只有更加密集的棍棒击打声。他的意识开始模糊,视线被涌出的鲜血染成一片血红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的脑海中闪过的,不是那些权倾朝野的辉煌时刻,也不是火烧明堂的疯狂,而是许多年前,在一个温暖的午后,那个还只是太后的女人,温柔地为他梳理头发,轻声对他说:“小宝,以后,你就叫怀义吧,你要记住,朕的心意,就是你的心意。”
“心意……”他喃喃地吐出最后两个字,身体重重地倒在了冰冷的地面上,再也没有了声息。
武攸宁见他已经气绝,这才小心翼翼地从柱子后面走出来,用脚尖踢了踢他那具血肉模糊的尸体,确认他死透了之后,才长舒了一口气,对着屏风后方恭敬地禀报道:“启禀陛下,逆贼薛怀义,已经伏诛。”
屏风后面一片寂静,过了许久,才传来武则天疲惫的声音:“……处理干净些。就说他是在家中暴毙,尸身送去白马寺,让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去料理后事吧。”
“遵旨。”武攸宁躬身领命,随即指挥手下将薛怀义的尸体用一张破草席卷了,从偏门悄悄运出宫去。大殿里的血迹很快被清洗干净,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而在另一座灯火通明的大殿——长生殿内,武则天正端坐在御座之上。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穿着宽松的寝袍,而是身着一身庄重的玄色朝服,头戴帝冠,神情肃穆。上官婉儿侍立一旁,大气也不敢出。刚才瑶光殿那边的动静,虽然隔得远,但那几声凄厉的惨叫,还是隐约传了过来。
“婉儿,你说,朕是不是太狠心了?”武则天突然开口,声音里听不出一丝波澜。
上官婉儿心中一颤,不知该如何回答。说“是”,那是质疑君主;说“不是”,又显得太过冷血。她思索片刻,低声说道:“陛下行的是雷霆手段,怀的是菩萨心肠。薛怀义火烧明堂,已是自取灭亡。陛下赐他一个体面的死法,已经是法外开恩。”
“体面?”武则天自嘲地笑了笑,“被乱棍打死,算什么体面?朕只是不想让天下人看朕的笑话罢了。一个被废黜的男宠,因为争风吃醋而烧毁了帝国最重要的建筑,传出去,朕的威严何在?大周的颜面何在?”
她站起身,缓缓走到窗前,看着外面沉寂的夜空。那片废墟的轮廓,在月光下显得更加狰狞。“他不懂,他从来都不懂。朕给他的宠爱,是恩赐,也是枷锁。他可以享受这份恩赐,但绝不能试图挣脱这副枷锁。他以为朕对他的情爱,可以凌驾于皇权之上。天底下,哪有这样的道理?”
她的声音变得愈发冰冷:“明堂,是朕君权神授的象征。天堂,是朕弥勒降世的证明。他烧了它们,就是烧了朕的根基。朕若不杀他,何以震慑天下?何以告慰神明?何以面对满朝文武?”
上官婉儿跪伏在地,深深叩首:“陛下圣明。”
武则天没有再说话,只是静静地站着。她的脑海中,浮现出薛怀义年轻时的模样。那个时候的他,充满了生命力,像一团火焰,温暖了她孤寂的深宫岁月。他为她督造明堂时的意气风发,他呈上《大云经》时的得意洋洋,他率军出征突厥时的英武身姿……一幕幕,都还历历在目。
曾几何时,她也曾真心实意地对他好过。她将他从一个市井小民,一步步扶上高位,给了他所能给予的一切。她容忍他的粗野,包容他的无知,甚至默许他的骄横。她以为,这份特殊的感情,可以成为她冰冷权力世界里的一点慰藉。
但她错了。权力场上,从来没有纯粹的感情。她给予的宠爱,被他当成了索取无度的资本;她给予的权力,被他当成了无法无天的依仗。当他的欲望膨胀到威胁皇权本身时,他们之间那点脆弱的情分,便不堪一击。
“帝王,注定是孤家寡人。”她轻轻地叹了口气,眼神中的最后一丝温情也随之消散,取而代之的,是属于帝王的、绝对的冷静和理智。“他只是朕手中的一颗棋子,既然已经失去了作用,甚至开始反噬主人,那就必须被清除。婉儿,你记下,明日早朝,朕要宣布三件事。”
“奴婢遵旨。”
“第一,追封苏良嗣为特进,以表彰其刚正不阿。朕要让天下人都知道,顶撞过薛怀义的,有赏。”
“第二,凡是薛怀义在洛阳城中剃度的所谓‘僧人’,全部捉拿归案,审问其不法之事,该杀的杀,该流放的流放。朕要将他的势力,连根拔起。”
“第三,传旨工部,立即开始明堂和天堂的重建工程。图纸要重新设计,规模要比以前扩大一倍,名字也改了,就叫‘通天宫’。朕要让所有人看到,一座明堂倒下了,朕能建起一座更雄伟的通天宫。一个薛怀义死了,对朕,对大周,毫无影响。”
上官婉儿一边听,一边用笔记下,心中却掀起了惊涛骇浪。这三道旨意,一道比一道狠辣,一道比一道决绝。第一道,是在为被薛怀义欺压过的百官出气,收拢人心。第二道,是斩草除根,彻底消除薛怀义的残余影响。第三道,则是向全天下宣告她的强大与不可战胜。
这就是武则天,一个将政治权谋运用到极致的女人。她的心中,没有男女之情,只有君臣之义;没有爱恨缠绵,只有利弊权衡。薛怀义的死,对她而言,不是失去一个情人,而是清除一个政治上的隐患,完成一次权力的洗牌。
第二天,薛怀义暴毙的消息传遍了洛阳城。朝堂之上,百官噤若寒蝉。当武则天面无表情地宣布那三道旨意时,所有人都明白了。那位曾经权倾朝野、连宰相都敢殴打的鄂国公,已经彻底成了一段过去。宰相苏良嗣听到自己被加封的消息,只是平静地出列谢恩,脸上看不出丝毫得意之色。他比谁都清楚,这并非对他的奖赏,而是女皇借他之名,在向天下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。
薛怀义的那些“净众”们,一夜之间从横行霸道的恶棍变成了阶下囚。洛阳城的百姓们,无不拍手称快。白马寺里,薛怀义的尸体被草草安放。那些曾经靠着他作威作福的“徒弟”们,此刻都作鸟兽散,生怕被牵连进去。最后,还是武则天派人,将他的尸骨胡乱烧了,骨灰混着泥土,送到了西边的大山里埋葬,连个坟头都没有留下。
薛怀义死后没多久,宫中又出现了新的面孔。一对年轻俊美的兄弟——张易之和张昌宗,经由太平公主的推荐,进入了皇宫。他们比薛怀义更年轻,更懂得如何讨女皇的欢心。他们能歌善舞,通晓音律,举止优雅,很快就取代了薛怀义的位置,成为了武则天晚年最宠信的男伴。
上官婉儿看着这对新贵在宫中平步青云,看着他们重复着薛怀义曾经走过的路,心中充满了感慨。历史,似乎总是在不断地重演。女皇需要的,从来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人,而是一个能够填补她情感和生理需求的角色。这个角色,昨天是薛怀义,今天是张氏兄弟,明天,可能又会是别人。他们就像是开在权力悬崖边的花朵,虽然鲜艳,却随时可能坠入万丈深渊。
几年后,新的“通天宫”在明堂的废墟上拔地而起。它比原来的明堂更加高大、更加华丽,直插云霄,仿佛真的能与天沟通。武则天站在新建成的宫殿之巅,俯瞰着脚下繁华的都城和壮丽的江山。此时的她,已经年近八十,脸上的皱纹更深了,步履也有些蹒跚。
她看着这座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建筑,眼神复杂。她想起了那个曾经为她督造第一座明堂的男人。那个男人,粗野、狂妄、愚蠢,却也曾带给她片刻的欢愉和慰藉。但最终,他还是被她亲手埋葬了。他的死,为她清除了障碍,巩固了皇权,也让她彻底明白了帝王的孤独。
站在权力之巅,她拥有一切,也失去了一切。亲情、友情、爱情,这些凡人的情感,对于一个帝王来说,都是奢侈品,甚至是致命的弱点。她必须时刻保持警惕,将所有可能威胁到她统治的人和事,都毫不留情地抹去。
晚风吹来,带着一丝凉意。上官婉儿走上前,为她披上一件斗篷。“陛下,起风了,该回宫了。”
武则天没有动,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:“婉儿,你说,后世会如何评价朕?”
上官婉儿沉默了。她知道,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。功过是非,自有后人评说。但她知道,在关于这位女皇的无数传说中,薛怀义的故事,注定会成为其中最富戏剧性、也最令人警醒的一笔。
他如同一颗流星,借着女皇的光芒划破了盛唐的夜空,璀璨夺目,却又转瞬即逝。他的崛起与覆灭,都源于同一个人,源于那份被权力扭曲了的、畸形的爱。
最终,武则天还是缓缓地转过身,走下了通天宫。她的背影在夕阳的余晖中,被拉得很长很长,显得无比威严,也无比孤单。她不需要别人的评价,她自己,就是一部活着的历史。
薛怀义的死,不过是她漫长而辉煌的政治生涯中,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。他的那把妒火,烧毁了有形的明堂,却也淬炼了女皇无情的帝王之心。在这座权力的熔炉里,情感永远是第一个被烧成灰烬的东西。这位独一无二的女皇帝,独自一人,继续统治着她的庞大帝国,她的心,也如同她身后的宫墙一般,冰冷而坚不可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