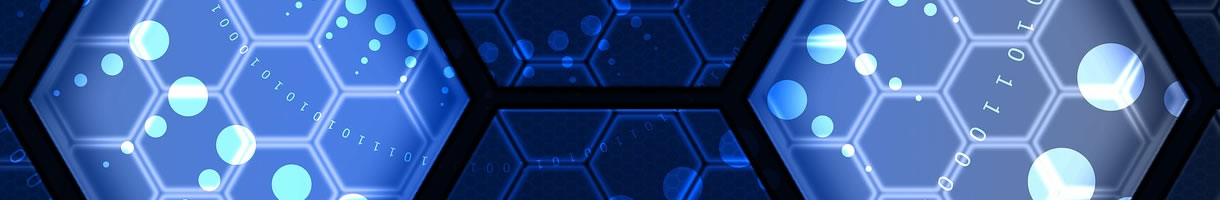莫斯科停工潮升级,25万核能职工两个月未发工资
当一个国家的核盾牌都护不住自己工人的饭碗时,这到底意味着什么?
伊万,一个在核电站干了一辈子的老工程师,最近总在莫斯科郊外的宿舍楼下抽闷烟。他曾是国家的骄傲,胸前挂过勋章,名字上过单位的光荣榜,连普京来视察时,他还作为工人代表握过手。可现在,这些荣耀换不来一度电、一滴水。宿舍楼已经停水停电快一个月了,楼道里垃圾堆得快要漫出来,那股味道让他阵阵作呕。

更让他糟心的是,昨天宿舍管理员直接下了最后通牒,再不交住宿费,就得被保安“请”出去。伊万手里攥着那张已经毫无意义的工资条,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他应得的薪水,但这笔钱,他已经两个月没见到了。他望向不远处那座曾经让他引以为豪的核工厂,如今那扇刻着镰刀锤头标志的铁门,锁住的不仅是机器,还有像他一样25万人的生计。
这事儿要是发生在某个犄角旮旯的小厂,大家可能骂几句也就认了。但坏就坏在,这可是国家的“心脏”产业,是俄罗斯在全球舞台上为数不多还能挺直腰杆的资本。
连这里都开始烂了,那其他地方呢?伊万的遭遇,显然不是孤例。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,不是为了喊什么口号,诉求极其卑微——把欠的工资给我们,让我们能吃上饭。罢工的横幅上,没有政治,只有最原始的生存呐喊。
这股寒气,早已从核工厂弥漫开来。顺着莫斯科环城公路往外开,你能看到越来越多熄火的工厂。一家本地挺有名的“小熊”牌巧克力工厂,前段时间还因为推出一款新口味而上了新闻,现在大门紧锁,门口贴着法院的封条。听人说,是因为从非洲进口可可豆的成本涨了三倍,老板实在是扛不住了。

还有一家给军队供应轮胎的大厂,按理说这种订单应该稳如泰山,可也停了。里面的朋友偷偷说,生产轮胎需要一种特殊的化学添加剂,以前都是从德国进口,现在路子断了,国产的替代品质量不过关,造出来的轮胎跑不了几百公里就得报废,这谁敢用?于是,整个生产线只能趴窝。
这种“铁锈”正在肉眼可见地蔓延。以前周末热闹非凡的购物中心,现在空荡荡的,三层楼的店铺关了一半。街上那些曾经需要排队的餐厅,现在服务员比顾客还多。失业的人们无处可去,只能在公园的长椅上发呆,眼神空洞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。
钱呢?钱都去哪儿了?这是一个所有人心中的疑问。其实答案并不复杂,只是没人敢公开说。你可以把整个国家想象成一个大家庭,这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卖石油和天然气。前几年油价高,日子过得还挺滋润。但现在,最大的买家欧洲不买了,只能打折卖给亚洲的朋友,收入直接腰斩。
与此同时,家里有个“吞金兽”,就是那场打到现在还没停的“特别军事行动”。每天睁开眼,光是弹药、军饷、装备损耗,就是一笔天文数字。据说,一天烧掉的钱,足够让伊万和他的25万个同事,舒舒服服地领上十年工资。收入在减少,开销却在无底洞般地增加,这个家底,怎么可能不被掏空?

为了填窟窿,央行只能玩命印钱。可印出来的卢布,在老百姓眼里越来越像废纸。官方牌价还硬撑着90卢布兑1美元,但在黑市,这个数字早就变成了400。
我一个朋友想给他孩子买一种进口的抗癌药,跑到黑市换美元,结果发现自己一个月的工资,连一小瓶药都买不起。这就是货币贬值最真实的写照,它不是新闻里的数字,而是压在每个普通人身上的大山。
面对汹涌的物价,央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加息,把利率死死钉在16.5%的高位。他们说这是为了控制通胀。这就像一个发高烧的病人,医生不去找病因,反而让他猛吃冰块。
体温是暂时降下来了,但五脏六腑都被冻得半死。那些嗷嗷待哺的企业,就是被冻伤的器官。三分之一的利润要拿去还银行利息,谁还敢扩大生产?谁还敢投资?活着,成了唯一的目标。

更魔幻的是,经济秩序正在倒退回最原始的形态。前几天,新西伯利亚的一家钢铁厂和本地一家食品罐头厂达成了一笔交易,钢厂给罐头厂一批钢材,罐头厂则提供几千箱牛肉罐头,用来给工人发福利。整个过程,没有一分钱的流动。
这种“以物易物”的现象,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叶卡捷琳堡的一家建筑公司,用手里的混凝土去加油站换柴油;乌拉尔的一家服装厂,把积压的几仓库冬衣,拿去跟农场换了土豆和面粉。这听起来像不像上世纪计划经济末期的笑话?
当人们宁愿用东西换东西,也不愿意接受货币时,这其实就是对整个国家信用的公开“不信任投票”。钱,已经不再是那个值得信赖的等价物了。
这种原始的交易方式,看似解决了燃眉之急,实际上却在把经济割裂成一个个孤岛,让整个市场变得更加混乱和低效。没有了统一的价值衡量标准,一切都乱了套。

傍晚,伊万又走到了宿舍楼下,点燃了今天最后一根烟。他抬头看着远方,克里姆林宫的尖顶在夜色中依然灯火辉煌,广播里还在播放着振奋人心的“胜利”消息。但伊万的脑子里,想的不再是那些宏大的叙事,而是明天,拿什么给远在家乡的妻子和孩子买早餐。
当一个国家最坚固的“核盾牌”,都开始从内部生锈时,它究竟还能抵挡什么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