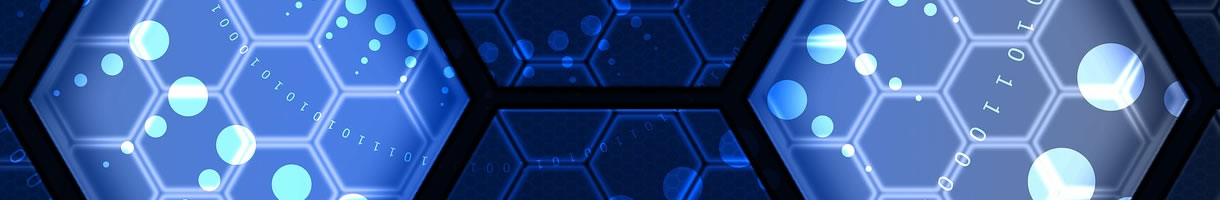朱元璋收下胡惟庸进的稀世砚台,夸 “辅政得力”!胡惟庸离殿后,他对徐达密言:此人权欲过盛,必除之
本文故事脉络参考《明史》、《明太祖实录》等相关史料。部分情节与观点为文学创作,请理性阅读。
洪武十三年的早春,应天府的寒意尚未完全褪去。奉天殿内的金砖地面,反射着一种冰冷而威严的光泽,一如御座上那位帝王的眼神。
朱元璋,大明王朝的开创者,此刻正用一种近乎漠然的目光,审视着匍匐在地的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。
胡惟庸的额头紧贴着冰凉的金砖,双手高高举起,托着一个紫檀木匣。
“启奏陛下。”他的声音平稳,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恭敬,“臣偶得一方稀世龙纹端砚,此砚历经前朝战火而无损,实乃天降祥瑞,佑我大明万年。臣不敢私藏,特献于陛下,以备陛下挥毫泼墨,批阅天下。”
太监小心翼翼地上前,接过木匣,呈递到朱元璋的御案上。
木匣打开,殿内响起一片极轻微的吸气声。
那是一方近乎完美的端砚,石色紫中带青,细腻如婴儿肌肤。最令人叫绝的是砚台上的天然石纹,竟浑然天成地构成了一幅“潜龙出水”图,龙鳞片片,龙爪张扬,仿佛下一刻就要破石而出。
朱元璋的目光在那方砚台上停留了片刻。
他的手指粗糙,布满了早年征战和务农时留下的老茧。他轻轻抚摸着砚台冰冷滑腻的边缘,动作很慢。
大殿之内,静得能听见香炉中沉香燃烧时发出的轻微“噼啪”声。
“好。”朱元璋终于开口了,声音嘶哑,听不出喜怒。
他抬眼看向胡惟庸,胡惟庸依旧保持着谦卑的姿态,似乎连呼吸都放轻了。
“胡爱卿,你有心了。”朱元璋的脸上缓缓露出了一丝笑容,但这笑容并未抵达眼底,“中书省事务繁杂,你身为百官表率,处置得井井有条,天下能有今日之安稳,你居功至伟。”
“臣惶恐。”胡惟庸叩首,“此皆陛下天威浩荡,臣不过是奉旨行事,不敢居功。”
“赏。”朱元璋挥了挥手,“辅政得力,理当有赏。这方砚台,朕很喜欢。”
“谢陛下隆恩!”胡惟庸再次叩首,声音中透出难以掩饰的喜悦。
“平身,退下吧。”
“臣告退。”
胡惟庸站起身,躬着身子,一步一步倒退着离开了奉天殿。他的背影挺拔,官袍上的一品仙鹤图案在幽暗的大殿中显得格外鲜艳。
他没有看到,在他转身的那一刻,朱元璋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。
皇帝的目光重新落在那方华美绝伦的砚台上,眼神变得锐利如刀。他拿起砚台,对着光亮处仔细端详,手指却猛地收紧。
“传。”朱元璋的声音压得很低,“宣魏国公,徐达,武英殿见驾。便服。”
“遵旨。”

01
武英殿,是朱元璋日常处理政务和私下召见心腹臣子的地方,远不如奉天殿那般威严,却更显私密。
徐达赶到时,已是午后。
他脱去了沉重的朝服,只穿了一身藏青色的常服,显得像个敦厚的富家翁,而非那个战无不胜的大将军。他一进门,就看到朱元璋正站在一幅巨大的《寰宇全图》前,背着手,一动不动。
御案上,那方稀世的龙纹端砚,在午后的阳光下,反而透着一股寒气。
“臣,徐达,参见陛下。”徐达没有行跪拜大礼,这是朱元璋特许的,他们是兄弟,更是过命的交情。
“天德,你来了。”朱元璋转过身,神色疲惫,“赐坐。”
“谢陛下。”徐达依言坐下,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被那方砚台吸引。
“看看这个。”朱元璋指了指砚台。
徐达起身,走上前,拿起砚台仔细端详。他虽是武将,但也识得好歹。“好东西。石质温润,雕工……不,这是天成的。潜龙出水,好兆头。”
“是啊,潜龙出水。”朱元璋冷笑一声,接过了话头,“胡惟庸早上进献的。满朝文武,都说这是祥瑞。”
徐达心中一凛,他听出了朱元璋话语中的森寒。
“陛下……”
“天德,你我相识多少年了?”朱元璋突然问道。
“臣自濠州追随陛下,至今已有二十六年。”徐达恭敬地回答。
“二十六年。”朱元璋走到徐达身边,拍了拍他的肩膀,“这二十六年,朕这双手,握过锄头,拿过饭碗,最后握住了这把刀,才有了今天的大明江山。”
他伸出那双布满老茧的手:“可你看,这双手,配得上这么精美的砚台吗?”
徐达心中巨震,他瞬间明白了症结所在。
“陛下,胡相他……”
“他不是胡相。”朱元璋打断了他,“他是中书省左丞相。是百官之首,是朕的辅政。”
皇帝走回御案后,缓缓坐下,双手十指交叉,放在那方砚台之上。
“天德,朕登基这十二年,睡过几个安稳觉?”朱元璋的声音里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,“李善长,朕忍了他多少年?如今换了个胡惟庸,你以为,他比李善长好吗?”
徐达沉默了。
李善长是开国第一功臣,权势熏天,最终也因“骄狂”而被朱元璋罢相。胡惟庸是李善长的继任者,也是李善长的同乡。
“胡惟庸比李善长更可怕。”朱元璋一字一句地说道,“李善长要的是功名,是体面。而胡惟庸,他要的是权。”
“这方砚台,不是一个臣子该有的东西。这东西的来路,比它本身更让朕心惊。”朱元璋的眼睛眯了起来,“他是在告诉朕,他胡惟庸能得到天下人得不到的东西。他是在炫耀他的门路,他的人脉,他的势力。”
“陛下,或许胡相只是想……孝敬陛下。”徐达艰难地辩解道。
“孝敬?”朱元璋笑了,笑声冰冷,“天德啊,你还是个实诚人。你知不知道,现在中书省的奏章,有多少是朕没看过,胡惟庸就敢直接批复的?”
徐达大惊失色:“他敢!这是僭越之罪!”
“他当然敢。”朱元璋的手指重重地敲击着砚台,“他以为朕离了他,这大明就转不动了。他以为他是谁?他是始皇帝的丞相李斯吗?还是汉武帝的丞相田蚡?”
朱元璋猛地站起身,在殿内来回踱步。
“朕设立中书省,是让他们辅佐朕。可现在,这个胡惟庸,他想做朕的‘仲父’!”
“辅政得力?”朱元璋想起早朝时自己说的话,脸上满是讥讽,“他辅政,辅的是他胡家的政!他得力,得的是他胡党的力!”
徐达屏住了呼吸。
他知道,皇帝是真的动了杀心。
“天德。”朱元璋停下脚步,回过头,目光灼灼地盯着徐达。
“臣在。”
“胡惟庸在朝中党羽众多,根深蒂固。朕若此时动他,朝局必将大乱。”
朱元璋走回御案,拿起那方砚台,在手中掂了掂,又重重放下。
“此人权欲过盛,必除之。”
这几个字,朱元璋说得很轻,却让徐达感觉比千军万马的冲杀还要冰冷。
“陛下圣明。”徐达低下了头,“只是,胡相并无明显大错,若要除之,恐怕……难以服众。”
“所以朕才叫你来。”朱元璋的眼神变得幽深,“朕要你帮朕看住京营。看住那些武将。”
“臣遵旨。”徐达毫不犹豫地应下。
“还有。”朱元璋压低了声音,“朕的‘拱卫司’,最近盯上了一些有趣的事情。胡惟庸的儿子,在濠州老家横行霸道。胡惟庸本人,似乎和一些‘故人’走得很近。”
徐达心中一跳。他知道,皇帝口中的“故人”,绝不是什么好词。
“朕需要一个契机。一个让他万劫不复,让满朝文武都无话可说的契机。”朱元璋的手,再次按在了那方龙纹端砚上。
“在此之前,朕要让他爬得更高,摔得更惨。”

02
时间进入洪武十三年夏。
天气越发炎热,应天府的官场却比这酷暑还要焦灼。
左丞相胡惟庸的权势,正如日中天。
朱元璋似乎完全忘记了武英殿中对徐达的那番密言。他对胡惟庸的恩宠与日俱增,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。
朝廷的人事任免,胡惟庸的意见往往能一言九鼎。各地送来的奇珍异宝,皇帝赏赐给胡惟庸的份例,甚至超过了宫中的皇子。
胡府门前,车水马龙,前来拜谒的官员几乎踏破了门槛。
“胡相。”一名中书省的舍人,小心翼翼地将一份奏折递给胡惟庸,“这是御史中丞刘基病逝前最后一道封奏,据说是弹劾……弹劾相爷您的。”
胡惟庸正在自己的书房内,欣赏着一幅前朝的名画。
他头也没抬,只是“嗯”了一声。
“相爷,这份奏折……是否要压下?”舍人试探着问。
刘基,就是刘伯温,曾经是皇帝身边最倚重的谋臣,但晚景凄凉。他死在应天,死因成谜,但官场上早有风言风语,说与胡惟庸脱不了干系。
“刘伯温?”胡惟庸终于放下了画卷,接过那份奏折。
他看都没看,直接扔进了身旁的火盆里。
“死人的话,陛下是不会听的。”胡惟庸淡淡地说,“况且,一个失了圣心的老臣,他的话,有分量吗?”
“相爷说的是。”舍人连忙附和,“只是……最近拱卫司的人,似乎盯上了咱们。”
“拱卫司?”胡惟庸的眉毛挑了一下。
那是皇帝的私人卫队,由都指挥使毛骧统领。这群人像黑夜里的蝙蝠,无孔不入,专门替皇帝办一些见不得光的事。
“一群鹰犬罢了。”胡惟庸不屑地冷哼一声,“让他们盯。我胡惟庸行得正,坐得端,难道还怕他们不成?”
“只是……”舍人有些犹豫,“听说他们最近在查吉安侯陆仲亨,还有平凉侯费聚……这二位侯爷,可都是相爷您的至交好友。”
胡惟庸的脸色沉了下来。
陆仲亨和费聚,都是手握兵权的武将。他拉拢这些人,确实花了不少心思。
“陛下这是什么意思?”胡惟庸在书房中踱步,“一边重用我,一边又来敲打我?”
“相爷,会不会是……”舍人压低了声音,“陛下对您,有所忌惮?”
“忌惮?”胡惟庸停下脚步,脸上露出一丝自负的笑容,“他当然该忌惮我。没有我胡惟庸,这满朝文武,谁能替他弹压得住?没有我,这大明的政务,谁能处置得如此顺畅?”
“他朱元璋,不过是个泥腿子出身的武夫。他懂什么治国之道?”胡惟庸的声音里充满了轻蔑,“他能坐上那个位置,靠的是我们这些淮西勋贵!”
“相爷慎言!”舍人大惊失色,慌忙跪下。
“怕什么。”胡惟庸坐回太师椅上,“这里是你我的心腹之地。你记住,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他朱元璋能坐上去,自然也能……”
他没有把话说完,但眼中的寒光已经说明了一切。
“传我的话。”胡惟庸沉吟片刻,“让陆仲亨和费聚最近安分一点。还有,告诉他们,如果拱卫司的人敢动粗,不必客气。”
“这……这是要和拱卫司正面冲突?”
“冲突?”胡惟庸冷笑,“毛骧敢吗?他不过是陛下养的一条狗。打狗,也得看主人。我就不信,陛下会为了一条狗,来责罚我这个‘辅政得力’的丞相。”
胡惟庸的算盘打得很精。
他料定朱元璋需要他来制衡朝中的武将集团,也需要他来安抚淮西勋贵。只要他不公然谋反,皇帝就奈何不了他。
而此时的皇宫深处,武英殿。
朱元璋正在听取拱卫司都指挥使毛骧的密报。
毛骧全身笼罩在黑色的飞鱼服中,跪在地上,声音嘶哑。
“陛下,胡惟庸的党羽已经渗透到了六部。兵部侍郎、户部侍郎,皆是其心腹。”
“他还私下接触陆仲亨、费聚等武将,结为异姓兄弟,往来频繁。”
朱元璋面无表情地听着。
“他还做了什么?”
“他还……”毛骧犹豫了一下,“他还派人……去了东瀛,联络倭寇。并且,臣等截获密报,他似乎与北元残余势力,也有勾连。”
“什么!”朱元璋猛地拍案而起。
“证据确凿吗?”
“……尚不确凿。”毛骧低下了头,“胡惟庸行事极为谨慎,臣等只能查到蛛丝马迹。他派往东瀛的人,在海上失踪了。与北元的联系,也只是通过一个皮货商人,尚未有实质性的文书往来。”
朱元璋的胸口剧烈起伏。
他知道胡惟庸有野心,但他没想到,胡惟庸的野心已经大到了这个地步。勾结外敌,这是灭九族的大罪。
“好,好一个胡惟庸。”朱元璋气得笑了起来,“朕还是小看他了。”
“陛下,是否现在就动手?”毛骧问道。
“不行。”朱元璋强迫自己冷静下来,“没有铁证,动不了他。他现在是丞相,党羽遍布朝野,冒然动手,只会逼反了他。”
“那……臣等该如何?”
“继续盯。”朱元璋坐了回去,眼中闪过一丝狠厉,“朕倒要看看,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”
“去查。”朱元璋压低了声音,“查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,胡霸。朕听说,他在濠州,可是威风得很啊。”
“臣遵旨。”毛骧磕了个头,身影如鬼魅般消失在殿中。
徐达从偏殿走了出来,他刚才一直在屏风后旁听。
“陛下。”徐达的脸色凝重,“胡惟庸这是在玩火。他连北元都敢碰。”
“朕不怕他玩火。”朱元璋冷冷地说,“朕怕的是,他这把火,会把朕的大明江山给点了。”
“天德,京营那边,你布置得如何了?”
“回陛下,京营十二卫,臣已换上八卫的指挥使。皆是跟随陛下多年的宿将,忠心不二。”徐达沉声回答。
“好。”朱元璋点了点头,“胡惟庸是文臣,他能倚仗的,不过是那几个被他拉拢的侯爷。只要京营在手,他就翻不了天。”
“只是,陛下。”徐达忧心忡忡,“臣担心,胡惟庸会狗急跳墙。他现在权势滔天,万一他孤注一掷……”
“他会的。”朱元璋的目光投向窗外,夏日的阳光刺眼而灼热。
“朕在等。等他自己露出马脚。”
“朕给他的恩宠,就是吊在他眼前的那块肥肉。他越是得意,就越会放松警惕。他越是以为朕离不开他,就越会肆无忌惮。”
“朕要的,不是一份似是而非的密报。”朱元璋的声音轻飘飘的,却带着血腥味,“朕要的,是满朝文武,都亲眼看到的……铁证。”

03
洪武十三年秋,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,打破了应天府表面的平静。
胡惟庸的独子胡霸,在濠州老家,因为强抢民女,争风吃醋,失手打死了人。
死者,是濠州卫所一名百户的亲弟弟。
百户一怒之下,聚众闹事,将胡霸扣押。濠州知府不敢得罪丞相,也不敢得罪军方,只能将此事八百里加急上报应天府。
奏折,先到了中书省。
胡惟庸看着奏折,气得浑身发抖。
“这个逆子!”他一巴掌拍碎了书案上的茶杯,“成事不足,败事有余!”
“相爷息怒。”中书省的舍人慌忙劝道,“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。此事可大可小。一个平民,死了也就死了。可偏偏,他是个军户,他哥哥还是个百户。”
“陛下最重军纪,此事若是闹到陛下面前……”
“他敢!”胡惟庸怒吼道,“他一个小小百户,敢扣押我丞相的儿子?他想造反吗?”
“相爷。”舍人冷静地分析道,“此事,恐怕没那么简单。背后……会不会是拱卫司在捣鬼?”
胡惟庸的怒火瞬间被浇灭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寒意。
他想起了毛骧那张毫无生气的脸。
“你的意思是,这是陛下设的局?”
“小的不敢妄言。”舍人低着头,“但濠州卫所,半年前刚换了指挥使。据说,那人是……徐达将军的旧部。”
胡惟庸的后背渗出了冷汗。
朱元璋和徐达。
“他们想用我儿子来要挟我?”胡惟庸的脸色变得狰狞,“好,好得很。不就是死了一个人吗?我赔他十条命!”
“相爷,万万不可。”舍人急道,“现在风头正紧。您若是强行施压,正中他们下怀。他们巴不得您犯错。”
“那我该怎么办?”胡惟庸烦躁地踱步,“难道真要我这儿子去偿命不成?”
“相爷。”舍人眼中闪过一丝阴狠,“事到如今,只能弃车保帅。不,连车都不能弃。”
“说。”
“您即刻上奏陛下,痛陈教子无方,请求陛下严惩逆子。”舍人说道,“您要表现得大义灭亲。”
“什么?”胡惟庸一愣,“要我主动请罪?”
“对。”舍人点头,“您越是请罪,陛下反而越不好动手。毕竟,您是丞相。陛下总要顾及您的颜面。”
“然后呢?”
“然后,您私下派人去濠州,重金安抚那名百户。只要他肯撤诉,此事便可化解。”
胡惟庸沉吟片刻,觉得此计可行。
“好,就这么办。”
然而,他还是低估了朱元璋的决心。
胡惟庸的请罪奏折递上去之后,犹如石沉大海,朱元璋既没有批复,也没有召见他。
整整三天,朱元璋都没有上朝。
一股压抑的气氛开始在朝堂上蔓延。胡惟庸派去濠州的人,也被当地卫所拦下,根本见不到那名百户。
胡惟庸开始真正地恐慌了。
他感觉自己仿佛陷入了一张无形的大网,而朱元璋,就是那个收网的猎人。
“不行,不能再等下去了。”胡惟庸在相府中坐立不安,“陛下这是要逼死我。”
“相爷,事已至此,只能兵行险着了。”舍人的脸色也一片惨白,“陛下迟迟不表态,就是在等。等我们自乱阵脚。”
“他想让我乱?我偏不乱。”胡惟庸咬了咬牙,“传我命令,让陆仲亨和费聚,以秋操演兵为名,向应天府靠近。”
“相爷!”舍人失声叫道,“您这是要……调兵?”
“不是调兵,是‘演兵’。”胡惟庸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,“陛下不是要看我的底牌吗?我就亮给他看。”
“他若敢动我儿子,我就敢让这应天府……换个天!”
胡惟庸的指令,通过秘密渠道,迅速传了出去。
他以为自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。
然而,他的一举一动,都在拱卫司的严密监视之下。
深夜,皇宫,武英殿。
灯火通明。
朱元璋和徐达正围着一张沙盘,沙盘上,清晰地标示着应天府周边的卫所部署。
“陛下,陆仲亨的部队已经离开驻地,正向溧水方向移动。费聚的部队也已开拔,直逼江宁。”
徐达的声音沉重如铁。
“好啊。”朱元璋的脸上看不出喜怒,“为了一个逆子,他竟敢私调兵马,威逼京师。朕这个丞相,真是‘辅政得力’啊。”
“陛下,陆、费二人皆是悍将,手下兵马加起来有三万之众。若他们真的作乱,京营虽然能胜,但也必是一场血战。”徐达忧心道。
“他们不敢。”朱元璋笃定地说,“他们只是在替胡惟庸壮胆。胡惟庸,还没那个胆子真的反。”
“那陛下打算如何应对?”
“等。”朱元璋的目光转向殿外深沉的夜色,“等他们靠近。等胡惟庸下一步的动作。”
“朕的网,已经撒下去了。就等他这条大鱼,自己撞上来了。”
就在这时,大殿的门被猛地推开。
毛骧,这位拱卫司的统领,第一次在朱元璋面前露出了惊慌失措的表情。他甚至忘了行礼。
“陛下!”毛骧的声音因为急促而变得尖利,他手中高举着一个用火漆密封的竹筒,“十万火急!臣等……截获了一封密信!”
朱元璋的瞳孔猛地收缩。徐达下意识地握住了腰间的剑柄。
“什么信?”
“是……是胡惟庸的亲笔信。”毛骧的声音在颤抖,“送往……送往北元大都!”
毛骧“扑通”一声跪下,双手将竹筒呈上:“信中……信中有胡惟庸的亲笔画押,还有……还有他许诺给北元的……应天府布防图!”
整个武英殿的空气,在这一刻彻底凝固了。
那封信究竟是真是假?胡惟庸难道真的已经疯狂到了这个地步?他勾连北元,是想里应外合,颠覆大明吗?而这一切,难道仅仅是开始……?
04
朱元璋的呼吸变得粗重。
他没有立刻去接那个竹筒,而是死死地盯着毛骧。
“胡惟庸的亲笔信?”他的声音嘶哑,仿佛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。
“千真万确。”毛骧从怀中又取出一份文件,“这是臣等从胡府书房暗中拓印的胡惟庸笔迹,与信中笔迹,一般无二。”
徐达走上前,从毛骧手中接过竹筒和拓本,转身呈递给朱元璋。
朱元璋一把扯过竹筒,捏碎了火漆封口,从里面倒出了一卷薄薄的丝绢。
他展开丝绢,徐达也凑了过来,两人借着烛光,逐字逐句地看了下去。
信的内容,比毛骧禀报的还要触目惊心。
胡惟庸在信中,不仅痛骂朱元璋“淮右布衣,窃据神器”,“刻薄寡恩,屠戮功臣”,还详细列举了应天府周边京营的兵力、粮草、将领姓名,以及换防时间。
他甚至向北元“故主”许诺,只要北元大军南下,他愿“率淮西子弟”,在应天府起事,“共襄盛举,重整乾坤”。
信的末尾,是胡惟庸的亲笔签名和私印。
“砰!”
朱元璋一拳砸在御案上,那方坚硬的龙纹端砚,竟被震得跳了起来。
“反了!他真的反了!”朱元璋的胸膛剧烈起伏,双目赤红,状若疯狂。
“陛下,息怒!”徐达急忙按住朱元璋的肩膀,“此事……有蹊跷。”
“蹊跷?”朱元璋一把甩开徐达的手,“铁证如山!笔迹是他的,私印是他的!布防图如此详细,除了他这个中书省丞相,谁能知道得这么清楚?”
“陛下!”徐达的声音猛然拔高,“胡惟庸是何等样人?他精明了一辈子,会蠢到在这个时候,留下如此明显的罪证?”
朱元璋猛地一愣,狂怒的火焰暂时被理智压下。
“天德,你什么意思?”
“陛下请想。”徐达冷静地分析道,“第一,胡霸之事刚出,陛下尚未表态,他胡惟庸已如惊弓之鸟。此时他私调兵马,已是行险。他怎敢在这时,再添上一条通敌叛国之罪?”
“第二,若他真要联络北元,岂会用如此原始的信使传递?他党羽众多,必有更隐秘的渠道。”
“第三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”徐达指着那封信,“这封信,写得太‘好’了。好得……就像是专门写给陛下您看的一样。”
朱元璋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。
他重新拿起那封信,仔细地又看了一遍。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朱元璋缓缓坐下,“这是个局中局?有人在陷害胡惟庸?”
“不。”徐达摇了摇头,“臣以为,这封信,或许是胡惟庸所写不假。但他写这封信的目的,恐怕不是真的要送给北元。”
朱元璋是何等聪明的人,他立刻明白了徐达的言外之意。
“他是想……试探朕?”
“或者说,他是在赌。”徐达沉声道,“他赌这封信会被拱卫司截获。他赌陛下您看到这封信,会投鼠忌器。”
“他私调兵马,是死罪。他通敌叛国,更是死罪。”朱元璋冷笑,“他凭什么认为朕会投鼠忌器?”
“因为……这封信里,提到了‘淮西子弟’。”徐达一针见血。
朱元璋的瞳孔再次收缩。
“淮西子弟”。
这四个字,是朱元璋的根基,也是他最大的隐痛。
大明朝的开国功臣,十有八九都出自淮西。他们抱成一团,同气连枝。胡惟庸,正是李善长之后的淮西文官之首。
“他是在威胁朕。”朱元璋的声音里,杀意沸腾,“他是在告诉朕,他若倒了,整个淮西集团,都会动荡!”
“他是在逼朕,在他儿子的命,和淮西集团的稳定之间,做一个选择。”
“好一个胡惟庸!好一个‘辅政得力’!”
朱元璋站起身,在殿内来回踱步,那方龙纹端砚,被他攥在手中,咯咯作响。
“陛下。”毛骧依旧跪在地上,不敢抬头,“信使如何处置?”
朱元璋停下脚步。
“杀了吗?”
“尚未。臣等将其扣押在拱卫司诏狱。”
“好。”朱元璋的脸上,突然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。
“天德,毛骧。”他招了招手,两人立刻凑了上去。
“朕,就如他所愿。”朱元璋压低了声音,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
“毛骧。”
“臣在。”
“你立刻回诏狱,’严刑拷打’那个信使。”朱元璋一字一句地说道,“务必让他‘招供’。招出胡惟庸指使他的全部‘罪行’。”
毛骧一愣,随即明白了皇帝的意思:“臣遵旨!”
“天德。”
“臣在。”
“你立刻回京营。传朕密旨,让那八卫指挥使,即刻全员戒备。但,只许在营中戒备,不许出营。”
徐达也明白了:“陛下是想……引蛇出洞?”
“不。”朱元璋摇了摇头,“朕是要……瓮中捉鳖。”
“胡惟庸不是想用淮西集团来压朕吗?朕就让他看看,他这个淮西领袖,到底有几分分量。”
“他不是想用北元来吓唬朕吗?朕就让他‘通敌叛国’的罪名,坐得实实的!”
朱元璋的目光,再次落回那封丝绢信上。
“这封信,不是写给北元的。也不是写给朕的。”
“这是胡惟庸写给自己的……催命符!”

05
胡惟庸的丞相府中,气氛压抑到了极点。
他已经整整两天没有合眼,眼球布满了血丝。
他派出去调兵的亲信没有回来。他派出去打探皇宫消息的眼线,也如泥牛入海。
那封送往北元的“投名状”,按理说,也该有回音了。
他不知道那封信是会平安抵达北元,还是会落入朱元璋的手中。
这本就是一场豪赌。
如果信到了朱元璋手里,朱元璋忌惮淮西集团哗变,必然会妥协,放过他的儿子,甚至会对他更加倚重。
如果信真的到了北元……那便是他最后的退路。
他唯一没有算到的,是朱元璋会如何利用这封信。
“相爷!”中书省舍人连滚带爬地冲进了书房,“不好了!不好了!”
“慌什么!”胡惟庸一把揪住他的衣领,“出了什么事?”
“宫里……宫里来人了!”舍人面无人色,“是拱卫司都指挥使,毛骧!他……他带着诏书来的!”
胡惟庸的心猛地沉了下去。
毛骧。
朱元璋的头号鹰犬,他亲自来宣诏,绝无好事。
“他来宣什么诏?”胡惟庸的声音在发颤。
“不知道……他只说,请相爷……即刻入宫面圣!”
胡惟庸松开了舍人,跌跌撞撞地退了两步,一屁股坐在太师椅上。
入宫?
这个时候入宫?
这是鸿门宴!
“不,我不去!”胡惟庸猛地站起来,“告诉他,我病了!重病!下不了床!”
“晚了……相爷。”舍人绝望地摇着头,“拱卫司的人……已经把相府给围了!”
“什么?”
胡惟庸冲到门口,只见庭院之中,黑压压地站满了身穿飞鱼服的拱卫司校尉,刀剑出鞘,寒光逼人。
毛骧,正站在庭院中央,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
“胡相。”毛骧的声音不带一丝情感,“陛下有旨,宣左丞相胡惟庸,即刻入宫,商议‘濠州百户通敌’一案。”
“濠州百户……通敌?”胡惟庸愣住了。
“不错。”毛骧缓缓展开一卷黄绫,“拱卫司查明,濠州卫百户张山,勾结北元,意图不轨。其弟之死,乃胡霸胡公子……义愤之下,为国除奸。”
“陛下圣明,查明真相。特召胡相入宫,商议如何……嘉奖胡公子。”
胡惟庸的大脑一片空白。
他那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逆子,成了为国除奸的英雄?
而那个百户,成了通敌的叛徒?
这是何等荒谬的逆转!
“不……这不可能。”胡惟庸喃喃自语。
“胡相。”毛骧的嘴角勾起一抹森冷的笑意,“陛下还在武英殿等着您。您……接旨吧。”
胡惟庸看着毛骧手中的诏书,又看了看周围杀气腾腾的校尉。
他知道,自己已经没有选择了。
这封诏书,是蜜糖,更是砒霜。
朱元璋用这种方式,告诉他,他儿子的命,保住了。
但作为交换,他胡惟庸的命,必须交出来。
“好。”胡惟庸深吸了一口气,强迫自己镇定下来,“老夫……接旨。”
他缓缓走下台阶,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冠。
他还是那个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的大明丞相。他要死,也要死得体面。
“毛都指挥。”胡惟庸平静地说道,“请容老夫……换一身朝服。”
“不必了。”毛骧打断了他,“陛下说,您这身常服,就很好。”
“胡相,请吧。”
丞相府的大门轰然打开。
胡惟庸在拱卫司校尉的“护送”下,一步一步,走向了那座他曾经呼风唤雨的皇宫。
应天府的百姓,远远地看着这支诡异的队伍。
他们看到,大明朝的丞相,面如死灰,走在囚犯一般的位置上。
他们知道,天,要变了。
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遍了应天府的官场。
那些曾经在胡府门前趋之若鹜的官员们,此刻都紧闭府门,人人自危。
陆仲亨和费聚的“演兵”部队,在距离应天府五十里外的地方,停滞不前。
他们接到了徐达派人送来的密信。
信中只有一句话:“陛下已知晓一切。尔等若敢再进一步,全家屠戮,片甲不留。”
两位手握重兵的侯爷,在权衡利弊之后,毫不犹豫地选择了……调转马头,撤回原防区。
胡惟庸的最后一张底牌,也失效了。
他所有的党羽,在朱元璋的雷霆手段面前,都选择了沉默。
那封威胁朱元璋的“淮西子弟”信,最终,只成了一个笑话。
06
武英殿。
朱元璋依旧坐在那张御案后。
那方龙纹端砚,依旧摆在他的手边。
徐达侍立在旁,全身甲胄,手按佩剑,如同门神。
胡惟庸被带了进来。
他没有被捆绑,也没有被呵斥,但他的精神,已经垮了。
“臣……胡惟庸,参见陛下。”他跪了下去,声音沙哑。
“胡爱卿,平身。”朱元璋的语气,一如既往的“和善”。
“谢陛下。”胡惟庸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。
“毛骧。”朱元璋没有看胡惟庸,而是转向了毛骧,“把信使的供词,念给胡相听听。”
“遵旨。”
毛骧从怀中取出一叠写满了字的宣纸,那是信使的“供词”。
“……罪臣张山,受北元伪帝册封,潜伏濠州……罪臣之弟,发现胡霸公子察知其阴谋,欲行灭口……反被胡公子所杀……”
“……罪臣为报私仇,并掩盖通敌罪行,遂诬告胡公子……”
毛骧一字一句地念着。
胡惟庸的脸色,从惨白,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潮红。
他知道,这每一个字,都是朱元璋在诛他的心。
“胡爱卿。”等毛骧念完,朱元璋才缓缓抬起头,目光落在胡惟庸的脸上,“你生了个好儿子啊。为国除奸,当赏。”
胡惟庸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。
“陛下……”
“只是……”朱元璋的话锋一转,声音陡然变冷,“朕有一事不明,想请教胡相。”
“臣……不敢。”
朱元璋从御案下,拿出了另一封信。
那封用丝绢写的,胡惟庸的亲笔信。
“这封信。”朱元璋将信扔在胡惟庸的面前,“也是你写的吗?”
胡惟庸看着地上那封熟悉的丝绢,瞳孔缩成了针尖。
他最后的侥幸,也破灭了。
“你一边让儿子为国除奸,一边自己却在通敌叛国。”朱元璋的声音不大,却字字如锤,砸在胡惟庸的心上。
“胡惟庸,你当朕是三岁的孩童吗?”
“你当满朝的文武,都是傻子吗?”
“扑通。”
胡惟庸再也站立不住,重重地跪了下去。
“陛下……臣……臣冤枉啊!”他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呼喊,“这是陷害!这是栽赃!臣对大明,忠心耿耿啊!”
“忠心耿耿?”朱元璋站起身,一步一步走到他面前。
“你结党营私,是忠心耿耿?”
“你权倾朝野,架空朕躬,是忠心耿耿?”
“你私调兵马,威逼京师,是忠心耿耿?”
“你勾结北元,出卖布防,图谋不轨,也是忠心耿耿?”
朱元璋每问一句,胡惟庸的身体就抽搐一下。
“不……不是的……陛下。”胡惟庸语无伦次,“臣……臣只是……只是想保住犬子性命,一时糊涂……那封信,是臣……是臣赌气写的,臣没想真的送出去啊!”
“赌气?”朱元璋笑了,笑声中充满了无尽的失望和杀意。
“好一个赌气。”
“你拿朕的大明江山赌气!”
“你拿淮西子弟的身家性命赌气!”
“胡惟庸啊胡惟庸,朕待你不薄,你为何,要反朕?”
“臣……臣没有反。”胡惟庸痛哭流涕,不住地磕头,“臣罪该万死,求陛下……看在臣辅政多年的份上,饶臣一命……”
“辅政?”朱元璋的目光,落回了御案上。
他走回去,拿起了那方精美绝伦的龙纹端砚。
“早朝时,朕夸你‘辅政得力’。”
朱元璋把玩着那方砚台,声音轻柔得可怕。
“朕当时就在想,这方砚台,这么美,这么滑。”
“它一定是吸饱了民脂民膏,才能如此温润吧。”
“它上面的龙纹,如此张扬,是不是……也和你的野心一样,想从这砚台里,爬出来,坐上朕的龙椅啊?”
“臣不敢!臣万万不敢!”胡惟庸魂飞魄散。
“你敢。”
朱元ž元璋的脸色,瞬间狰狞。
“你什么都敢!”
他举起那方砚台,用尽全身的力气,猛地砸向胡惟庸的头顶。
“砰!”
一声闷响。
砚台碎裂,胡惟庸的额头鲜血迸流。
他难以置信地抬起头,看着朱元璋,眼中充满了恐惧和怨毒。
“来人。”朱元璋扔掉手中残留的碎石,厌恶地擦了擦手。
“把这个……通敌叛国的逆贼,拖下去。”
“胡惟庸结党谋逆,罪证确凿,即刻……凌迟处死。灭九族。”
“不——”
胡惟庸发出了不似人声的惨叫。
他被两名如狼似虎的校尉拖了出去,鲜血和墨汁,在武英殿的金砖上,拖出了一道刺眼的痕迹。
徐达站在一旁,从头到尾,一言未发。
他看着地上的血迹,又看了看那些破碎的端砚残片,只觉得一股寒意,从脚底,直冲天灵盖。
07
胡惟庸的死,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巨石,在平静的大明朝堂,掀起了滔天巨浪。
这,仅仅是一个开始。
朱元璋以胡惟庸“通敌叛国”为由,下令彻查“胡党”。
拱卫司和新成立的“锦衣卫”,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,扑向了整个官场。
一场席卷大明,持续数年的血腥清洗,拉开了序幕。
数日后,早朝。
奉天殿内,弥漫着浓重的血腥气。
朝臣的数量,肉眼可见地少了两成。
那些空出来的位子,它们的主人,大多已经身在诏狱,或者,已经永远地闭上了嘴。
幸存的官员们,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。
朱元璋高坐龙椅,面色平静,仿佛前几日的血雨腥风,与他毫无关系。
“有事启奏,无事退朝。”太监尖利的声音响起。
满朝文武,一片死寂。
无人敢出列,无人敢抬头。
“既然众爱卿无事。”朱元璋缓缓开口了,“那朕,倒有一事,想和众爱卿商议。”
群臣的心,都提到了嗓子眼。
“自古以来,设丞相,辅佐天子,治理万民。”朱元璋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中回荡。
“朕,亦效仿古制,设中书省,任李善长、胡惟庸为相。”
“然,李善长骄狂,胡惟庸谋逆。”
“朕思来想去,深感不安。”朱元璋的目光扫过群臣,“丞相之权,过重。上,则欺君罔上;下,则残害百姓。”
“朕以为。”朱元璋顿了顿,声音变得无比威严。
“丞相之职,实乃……万恶之源。”
此言一出,满朝皆惊。
“朕意已决。”朱元璋不给任何人反对的机会,猛地站起身。
“自今日起,废除中书省,罢丞相之职!”
“朕,将亲揽大权。六部,今后直属朕躬,凡事皆由朕亲自裁决!”
“另,设‘四辅官’,为朕顾问。设‘殿阁大学士’,为朕批阅文书。”
“尔等,可有异议?”
威严的目光扫过,无人敢与之对视。
废除丞相,这是自秦朝以来,延续了千年的制度的终结。
皇权,将在这一刻,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。
群臣跪伏在地,山呼万岁。
“陛下圣明!”
朱元璋满意地看着匍匐在地的臣子们,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。
他赢了。
他不仅除掉了胡惟庸,更借着胡惟庸的案子,彻底打垮了淮西勋贵集团,也一劳永逸地,废除了那个敢于分他权力的丞相制度。
退朝后,武英殿。
徐达求见。
“天德,你来了。”朱元璋正在练字,神情愉悦。
“臣,参见陛下。”徐达的脸色,却带着一丝苍白和忧虑。
“陛下。”徐达犹豫再三,还是开口了,“胡党一案,牵连甚广。如今,已杀三万余人。京中,人人自危。臣恳请陛下……收回天威,宽恕那些胁从之臣吧。”
朱元璋的笔,停住了。
一滴浓墨,落在了宣纸上,晕染开来。
“三万人?”朱元璋淡淡地说,“多吗?”
“朕当年起兵,战死的兄弟,何止三十万?”
“胡惟庸谋逆,这些人,攀附于他,便是同党。不杀尽他们,如何能让天下人警醒?”
“可是,陛下……”徐达急道,“如此屠戮,恐伤国本啊!况且,株连九族,滥杀无辜,实非圣君所为。”
“圣君?”朱元璋放下笔,冷冷地看着徐达。
“天德,你告诉朕,什么是圣君?”
“朕若不狠,朕的江山,坐得稳吗?”
“朕若不杀,朕的子孙后代,能安枕无忧吗?”
朱元璋走到徐达面前,盯着他的眼睛。
“你以为,朕废除丞相,只是因为胡惟庸?”
“朕废的,是所有敢于觊觎皇权的人!”
“朕要的,是绝对的权力。朕要这大明江山,千秋万代,都姓朱!”
徐达在他的目光逼视下,缓缓低下了头。
他无话可说。
“你累了。”朱元璋的语气缓和了下来,“天德,你我兄弟一场,朕不想你卷进来。你年纪也大了,该歇歇了。”
“回你的魏国公府,颐养天年吧。”
徐达心中一寒。
这是……在剥夺他的兵权。
“臣……遵旨。”
徐达躬身告退。他走出武英殿,看着刺眼的阳光,只觉得浑身冰冷。
他知道,那个曾经与他并肩作战,同生共死的朱重八,已经彻底死了。
活着的,只有大明朝的开国皇帝,朱元璋。
大殿内,朱元璋重新拿起笔。
他看了看地上那些破碎的端砚残片,那是他特意让人留下的。
“辅政得力……”他喃喃自语。
他提起笔,在宣纸上,写下了四个大字。
“永不复设。”
从此,大明王朝,乃至后世的数百年,皇权被推向了极致。
而那方因“辅政得力”而被夸赞的稀世砚台,最终的归宿,不过是帝王猜忌下的一地碎片。
创作声明:本篇故事为虚构内容,如有雷同纯属巧合,采用文学创作手法,融合历史传说与民间故事元素。故事中的人物对话、情节发展均为虚构创作,不代表真实历史事件。